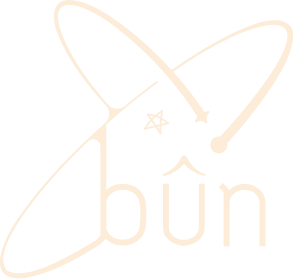我最近開始在思考「散文」這件事。
契機當然是關於十一月底林榮三文學獎的爭議,我閱讀了網路上我所能找到的文章,以相關關鍵字丟進臉書的搜索框和噗浪的搜索框,但凡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公開可見文章我全都拜讀過了。是的。全部。那對我並非難事。
基於過往個人的小小小興趣,在高中時從在網路上親見過「散文虛實之爭」的大型論戰,我透過碩博士論文網翻找了所有關於散文的研究與論述,而後懵懵懂懂地明白——「散文」可能是什麼?
而在二零二三年的林榮三爭議當中,經過文學院訓練,有了先備知識的我,很快地明白了事情的癥結點在哪裡。散文的問題(如果我們先承認它有問題),從來都不在於「散文的真實與虛構」、「散文能否虛構?」、「散文、小說與詩之間的越位與跨界」等問題,而是在於最根本的,與文學獎機制相關的問題,即「文學獎機制透過其本身生產文化意義的能力,哄誘諸多寫作者以自身真實或他者的真實去換取文化的資本或自身階級的向上提升」。
這是機制的問題,而非文學的問題。
為了讓普羅大眾讀懂這篇文章,我猜想我或許應該以類似論文的形式撰寫這篇文章(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做到這樣,還望海函)。我所使用的理論及方法如下,包含但不限於: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布迪厄的品味慣習及權力場域論述、行動者網路理論(ANT)、二元對立論、阿圖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及我在純文學場域和類型文學場域中同時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及評論者的自我敘事。
之發現這件事情,是起於一種遊戲的心態。我拿過一張紙,在上面粗略地畫下(或者說寫下)如下標籤:「菁英/非菁英」、「純文學/大眾文學(類型文學)」等字樣,然後開始思考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用以區別兩者的會是甚麼?以文學獎為例,最初的文學獎制度始於1970年代,那是美援文化後幾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與加工出口區的年代,擁有識字撰文的能力相當稀有,故擁有這些技能的人,在當初或許就會成為「得文學獎的人」。
到了1980年代,那是一個「台灣錢淹腳目」,識字的人變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較前一個十年變得更多的時代,那是一個還沒有解嚴的時代,所有文學都得收斂於一種安全的框架之中。於是,外文系的人著迷於現代主義、意識流等著重講述自己七罪墮落的故事;中文系的人發展出抒情美文,不談政治、不談家國思考、不談「嚴肅的話題」,而是談自己的感悟與人生。文字柔美詭麗而貼身,卻也只能貼身,否則撰寫文章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抒情美文會是一種當時寫作者們下意識要保護自己的寫作策略嗎?寫得「大」了會出事,寫得「小」又「個人」,經驗與書寫生命容易越寫越少,越大膽地揭露便是將自己與家人的私隱曝光於大眾眼下。普通人哪有那麼多故事可寫?哪有那麼多至親之人敢於傷害?於是為了填補篇幅,抒情的、美麗的句子與從各方引借的神話傳說故事於焉而生,唯有如此,才能把「自己」寫得少一點,又多寫幾回自己好鑄成一本本書。作家不靠賣書賺錢,要靠甚麼呢?
這會不是會某種文學家們在商業市場下的「自我保護機制」?潛意識以抒情美文保護自己。(請原諒我挪用卡爾·博蘭尼在《鉅變》一書所述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理論)。書寫不見得是療傷,有時反是傷害,這是散文文學的雙面刃。
如若寫散文如斯可怖、兩難。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地研究散文、書寫散文呢?原因無他,按照STS領域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NT),台灣的文學獎機制本身就會哄誘人們繼續寫散文投稿比賽。無論人們的動機是為了錢、為了文學名譽、為了挑戰自己……任何理由都好,人們的行為都不會改變文學獎這個機制本身只是在於蒐羅作品,以免去某個人或某個單位去尋找作品和簽授權的麻煩之功能。
不管外在的冠冕如何堂皇,文學獎的機制,真的,或許就只是這樣而已。
到了台灣已是全民大學生的此刻,菁英與非菁英的標準早已不是大學學歷,但文學獎機制隱含的慕強性格(也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排序的給獎方式),讓人們誤以為,唯有足夠真實才夠稱得上自己是菁英。「真實」遂成為一種貨幣,用以兌換更高階級的晉升權或兌換實際的獎金這類「真實貨幣」用以生活。
而人類的本性當中是有窺探慾的,故散文遂會成為旁人一窺他人人生的那一道門縫。在社群媒體尚未蓬勃發展的年代,聽說純文學圈賣得最好的是散文集。那到底代表著什麼意思?出版社主打、出版散文集到底是什麼意思?而當散文都以自身經驗寫成時,拿去投文學獎,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遂都只能從類似的文章中揀選。評審應該要如何列等每個人的經驗這件事?非當事人、非某一件事情詮釋的權威者,到底該如何在相似的散文之海中擇出最美善的水滴?我沒有答案。
散文文學獎是會複製自身直至自身滅亡的文體機制。我的意思是,單純出於「思考」的文章,而非「個人經驗」的文章,難道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就不能被稱之為散文嗎?這是我想叩問的事情。
而散文的「真實為上」之精神,同樣輻射到了純文學場域中小說的寫作。要夠真實(或者說看起來足夠真實)才稱得上是菁英,所以文學獎純文學比賽中,是不能出現「虛構」的,例如媽祖跟月老談戀愛、龍跟人類生下小龍女。通常它們被稱為大眾類型文學。我一直在想,被我們稱為大眾文學或類型文學的一切,是不是只是因為它們的篇幅超出文學獎短篇小說所需的字數(受報刊版面所限)?是不是只是因為他們讀起來「太虛構」或「不夠真實」?
取得「真實」跟取得「知識」一樣,都需要足夠的經濟、社會及文化資本。台灣民眾的的知識水準是一代比一代高的,我猜想這可能要歸功於大概十年改一次的課綱以及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吧!過去出身較為辛苦的孩子是難以接觸到高等教育的,但如今三十歲到四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們是可以不太費力就有大學可以讀的,於是這一群人回眸於他們的父母輩,撰寫出來的文學散文多多少少便帶了些社會學或各式文化理論思潮的意涵。
當我橫跨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寫作時,我在各種會議、講座與討論時發現一個我的小習慣,當我在大學演講或台文館演講時,我所使用的語彙是「田調」、「田野調查」;而當我在國際書展或言情小說出版社和編輯聊天時,我所使用的詞語是「查資料」。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我在我的言情小說編輯面前說出「田調」一詞時,她臉上困惑而又不好意思的神情。玟珒,「田調」是什麼?她想了許久,然後小心翼翼地問:妳是指查資料嗎?
這彷彿能叩問邏輯如何形塑語言。「田野調查」指的是實際走入當地,勞心勞力取得資料;而「查資料」則是坐在家中,從網路上就可以自訊息之海中蒐羅無線資訊。有些時候在學術圈,人們讚嘆前者,而沒那麼重視後者。但對非學術圈的人、年紀較長的人來說,能使用網路查到正確無誤資訊已經是非常厲害的事情了。
是的,田調、採訪之難,所以我們有時會將它視為做人文學問的最高標準,能做得到、捱住勞苦的人便是菁英。這不又是一種「真實=菁英=好」的遊戲嗎?又因為田野調查的成本極高,所以難以阻止部分人士藉此發展更多「副產品」,以他人的故事撰文投獎以此回收成本。
現在社會學家算是中產階級,而他們的父母在過去十年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不是。當我們期許社會學家是一面鏡子、一面玻璃能映出底層的生存樣貌時,有沒有可能,社會學者其實更像是「真實」與「知識」的物流廠?物流廠的意思是,在文學獎的場域中,機制誘使人們將他者的日常取走,按照中產階級的品味繕寫,轉化為弱勢者都看不懂的東西後,提供給中產階級的消費者(讀者),讓讀者「獲得新知」、「關懷弱勢」?有沒有可能,這世界上有那樣的一群人,是以旁觀別人的日常生活作為自己的休閒娛樂的呢?以散文或純文學小說的形式。如若旁人口中的奇觀與獵奇,實為某個人的日常所見。我們到底該如何自處?知識是該帶有傷害性質的嗎?
思考這些的時候,我彷彿明白了史畢娃克在寫〈底層可以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的心情。
有沒有可能,文學獎小說和文學獎散文其實並不存在過大的差異?有沒有可能,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那條界線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機制在作怪?有沒有可能,我們缺乏的從來就不是「經驗」,而是缺乏對某項機制或規則默契的全盤認識?有沒有可能,我們能不服從「真實=菁英=好」的規則,讓文學、讓文學獎變得更加創新及富有可能性?
當我們說出:「我說的/寫的/感受到的都是真的。」;當寫作者說出:「我真的寫出了別人的故事/那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
最近,我在思考「文學」與「教育」這件事情,也就是「作文」在學校教育中扮演的角色。
根據阿圖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有能力形構人們意識形態的機制有三:政府、媒體與教育。普遍認為讓孩子們受教育是為了讓他們有「更好的未來」,而「更好的未來」有時指的是階級的晉升,從底層往上爬至中產階級;從中產階級攀至貴族或富豪階級,那麼,已是金字塔頂端的貴族階級們要以什麼階級作為目標,繼續向上流動呢?
我想那可能會是「資助藝文的能力」、「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價值觀的能力」。在學校教育中,最容易被人們誤以為能達成此目標的方式大概就是透過「作文」這項訓練吧?我在乎的不在於「作文是否能寫真的事情/假的事情才會得高分」,我在乎的是「平平都接受過國民義務教育的作文訓練,為什麼仍有人分不清『真實』與『虛構』的差異、『散文』與『小說』」的差異?」,這當然能粗暴地用學校教育並不教人寫小說來回答,但這回答並不使我個人滿意,遂努力地想辦法生產一套能說服我自己的論述。
假設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階級的晉升、不輸在起跑點(話說這句話我也覺得奇怪,贏在起跑點但輸在終點會比較有意義嗎?),那麼目前坊間大多的作文教育都是建立在「真實=菁英=好」的邏輯上而實施教學的。從中文系畢業的老師們成為國文老師,將他們在學校所學到的價值觀、信仰體系與「自我修復機制」(然而,我們該如何證明某個人的潛意識當中現代科技難以觸及之處?我們該如何證明『無』本身?),被一代一代地權威式地傳授給小學到大學的學子們,讓這一套邏輯與價值體系得以更加鞏固、堅不可摧。
那麼,難道自有作文教育以來,我們的教育方式就都是錯的嗎?我認為不是,個人覺得我們只是在執行一套教育方式時需要顧及某一個機制的多面性。比方說:當我用在教作文如何「借物寓情」時,我們被教導要「將某件事物賦予意義,它才會產生意義」。人類如神,對物指稱而賦予了它名姓、價值、意義與重要性。然而這種「借物寓情」的寫作手法,同時也掩蓋掉了某物或某機制的本質,掩去它原本最「無機」、「無感情」的「功能」。在行動者網路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個系統中的所有事物都不比人高尚或低階,一切參與者都被置放於同一個水平面上,相互對彼此產生意義。
舉例而言,一條由前男友贈送的項鍊可能意義非凡,承載眷戀或怨恨。但無論人類對項鍊的情緒或觀感如何,都不會影響到項鍊本身是一條可被轉賣、可被丟棄、可被贈送與他人(?)的二手物品。
若能理解上述言詞,我會鼓勵閱讀這篇文章的人們使用同樣的邏輯思考文學獎機制,並得出自己的答案。
※
自我從十一月底思考出這些結論以來,我很快地意識到兩個巨大的問題:一是我正在質疑對許多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文學獎機制與散文;二是我等同於在說,如若這個哄誘的機制及早被人發覺,那麼,有沒有可能,許多散文寫作者在下筆前的痛苦、自我懷疑與傷人歉然都不是必然的?有沒有可能,當「真實=菁英=好」的邏輯被打破之後、藝文的巧言令色被打破之後,有許多的傷害都是可以避免的呢?不涉及自我揭露的文章,是否仍然能是一篇好的文學獎散文?有些時候小說(「虛構的代名詞」)和散文(「真實的代名詞」)的分類不在於為讀者考慮,而是在保護寫作者自身,那是純文學寫作者們在書籍公開發表後唯一的鎧甲。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無意破壞既存的文學獎機制。我不能因為我不是一個崇尚慕強價值的人而去意圖改變其他人對文學獎所象徵的尊榮與肯定之追求。維持現有的文學獎機制固無不可,我只是希望提醒人們機制本身會哄誘與生產對它自身有利的意義而已。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感到非常抱歉,我覺得我像個怪物破壞了我所愛的圈子。對我那些寫散文、寫純文學小說的朋友來說,我將他們花費多年時間與心力的研究成果盡數破壞。我等同於是在告訴他們,他們所追求的東西極有可能是假的、是虛幻的,不必以「真實」、以「親身經歷」做交換也有可能達成。凡事都能偽造,有時連「真誠」都能精心構築而成。當然獎金一定是真的,但他們用以兌換金錢的「貨幣」是他們的真實人生與摯親至友的私隱。我不知道這是否合算?
我不是特別聰明的人(我覺得我特別笨),我一定是發現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只是特別殘忍,把大家維持溫柔默契不說破的事情,說出來了而已。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選擇相信我不認識的、陌生的散文寫作者、研究者們有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克服他們自身的課題,祝福。我也不知道這一篇文章該放在何種脈絡下去討論,如若放在歷史論文中,它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容易被駁倒的第一手史料;如若放在文學論文中,它顯然不符合傳統研究抒情散文的論文形式;如若放在社會學論文來看,它僅是我的自我敘事且不符合真正嚴謹的論文格式。我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定義這篇文章了,所以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我只能說它是一篇散文。這就是我寫出來的散文。只有這樣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