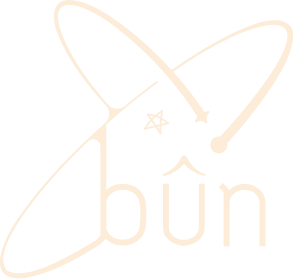跨越二十多年的積累——專訪《全臺詩》編輯團隊
(首刊於《閱:文學》雜誌NO.81「業界直擊」專欄)
《全臺詩》的編輯是由一群研究臺灣古典詩的學者、詩人、藏書家、民間人士等組成的團隊負責的,自2000年開始蒐集史料、詩作,慢慢整理編輯出版,目前已出版了七十餘冊。《全臺詩》的編輯流程究竟如何?本次「業界直擊」單元將帶領各位讀者前往工作室,直擊《全臺詩》編輯團隊的工作現場。
我們是一個團隊,團魂不滅!
走進《全臺詩》的工作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整面的書牆,倚牆而立的書櫃最上層陳列迄今出版的七十五冊《全臺詩》,其他的櫃子裡則擺滿工作所需的參考資料、學術書籍與刻印本。
「這些書只是一部份,我們樓上還有一個房間,裡面都是書。」編輯團隊這麼說。古典詩的保存耗時費力、校注嚴謹,無怪乎需要那麼多的書互相參照。
《全臺詩》的編纂是一項橫跨數十年的古典詩作保存計畫,從清代方志、日誌報刊、詩社資料與藏書家的藏品中蒐集鄭氏時期到戰前的古典詩,並為古典詩人做生平小傳。在計畫主持人施懿琳教授的帶領下,這一個計畫二十多年來已經過五、六代的團隊成員更迭。據編輯團隊所言,歷年來的工作夥伴除非是因為結婚、搬家等人生規畫改變,不得已才辭職,否則多數成員都可以一直做下去。以採訪當日受訪的兩位專任助理為例,一位已做了八年,且大學時期就在團隊中當工讀生,另外一位則在這裡工作近五年。舊人去,新人來,不斷地傳承、延續這一份臺灣古典詩的保存工作。
「收到你們的訪綱後,我們有去問之前在這邊工作的前輩們的回答,所以等一下回答的是一個統合起來的答案。」受訪的助理這麼說。
「喔,好。沒有問題。」我答。
得知事前訪綱的回答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蒐集而來後,我內心有點訝異,不免佩服起《全臺詩》工作團隊內部的緊密聯繫,其嚴謹的工作方式也從這次採訪的細節可略知一二。
《全臺詩》的計畫從2000年開始,彼時線上協作系統尚未普及,搜尋引擎也不太找得到臺灣古典詩的資料,古典詩文的蒐羅與建置全仰賴早期幾位臺灣文學學者的材料及研究,透過團隊人工判讀、登打的方式,將詩文打字輸入Word當中,建立初步的檔案資料庫。《全臺詩》的編輯團隊跟我們分享,以前在蒐集資料時會遇到版本不一的問題,可能同一首詩在A方志裡面記載的作者是甲,但在B方志中卻寫成乙。而之所以能發現這一點便是因為當初整理資料的前輩有印象在不同的資料中讀過同樣的詩句,進一步能查找、考證。在網路工具、AI技術不太發達的年代,個人的經驗與記憶便是工作時的絕佳利器。
另外需要依賴「人工智慧」的事情還有文字的辨認。古典詩的抄本有時是以草書寫成。草書難辨,便需要請書法專家按照前後文來辨析字句。在詩集的印刷過程中也常有錯字的情況,如「雨」寫成「兩」、「蜒」寫成「蜓」等。錯字辨認得多了,編輯團隊亦從中變身抓錯小達人,遇到文句不通時,資深者憑著經驗便可推理出詩句中大概又是哪個字被誤用了。
不過,編輯團隊也坦言,並不是每一次校對完《全臺詩》的書稿之後就不會有誤。「像《全臺詩》的第一冊,我們校對了好幾次,書出版之後還是有抓出很多錯誤。」編輯團隊一邊說,一邊向我們展示《全臺詩》第一冊上花花綠綠的便籤。我想,那上頭所貼著的每一張便籤,或許都代表著編輯團隊要求自身「下一本要更好」的期許吧!
他們從古典詩看到的風景
臺灣古典詩詞的研究在當今臺灣文學的領域中是較為冷門的專業,我好奇在《全臺詩》編輯團隊中工作的人們是起於什麼樣的動機而在此工作的?又於工作中獲得什麼樣的樂趣呢?
於團隊擔任專任助理工作了八年的謝宜珊說,在工作中會讀到許多日治時期文人的詩句,而她的祖父母是接受日本教育的一代,詩文中的內容讓她得以更接近祖父母過去的生活。另一位即將工作滿五年的專任助理張郁璟則分享自己旅遊時的經驗,日治時期的古典詩人很常到了某一景點就寫詩助興,紀念自己曾到此一遊。張郁璟說自己曾因為讀了某些詩而跑去詩中提到的地點觀光,熱門景點如北投溫泉、日月潭、阿里山、關子嶺等,冷門地點如芝山岩、石門戰場她都去過。
從古典詩的內容中不但能得知詩人的足跡,還能知道當時文人們的交友網絡,了解他們那時的生活。今昔對比,從中得到樂趣。《全臺詩》編輯團隊中有人特別喜歡讀清代的古典詩,從詩文中挖掘當時的中國文人是怎麼看待臺灣的。「當時有非常多官員來臺灣,用一種特別的眼光來描寫臺灣,以『異物書寫』的角度來描寫臺灣的物產、水果。」編輯團隊的前輩詳細地解釋著,「對現在的我來看,那些東西就是我從小吃到大的水果,平時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因為有那些清代詩人的書寫,我就會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一種觀看臺灣的方式,此一命題到了日治時期再度出現,但觀看者從中國人轉為日本人。《全臺詩》所整理的古典詩當中,或多或少都反映了當時的人們怎麼看待臺灣的這件事。對編輯團隊來說,從詩句中「再發現」新的觀看臺灣的視角不失為一個小小的樂趣。
「除了有趣的部份之外,編輯《全臺詩》的過程中有沒有感到無聊或煩燥的時候呢?」我這麼問編輯團隊,暗暗擔心這問題是否顯得冒犯?所幸編輯團隊答得爽快,且答案獲得全場一致認同。
「有啊!讀擊缽詩的時候。詩題一直重複很無聊欸!」
「而且就算是不同的人寫的,寫的詞彙、用的象徵都一樣。」
擊缽吟是一種日治時期文人逢年過節或相互酬作的文體,由主辦方訂定題目,參與者於一定時限內「命題作詩」,經過評比後,寫得最好的人可以獲得獎品或獎金。報刊雜誌有時也會舉辦擊缽吟比賽,有些文人為了想得獎就會寫很多首類似主題的詩,或冒用親戚的名字、編造不同筆名寫詩投獎。近百年後,當時文人所寫下的海量擊缽詩及曾使用過的名字都變成現在《全臺詩》編輯團隊在研究詩人與詩文時不得不閱讀、考證的資料。
「《全臺詩》目前的做法就是把古典詩當作是這個年代需要被保存的資料。現在沒興趣,說不定以後會有人有興趣啊!」《全臺詩》的編輯團隊笑了笑,「有一些東西如果現在不去整理它,之後要保存就更困難了。」饒是編輯過程繁瑣辛苦,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投注,《全臺詩》的編輯團隊仍不畏困難,二十多年如一日、一代又一代地為臺灣古典詩文的保存和研究貢獻心力,替未來的研究者們積累多元豐厚的文史土壤。